摘要:面对“我还有救吗”这个问题,李子勋教授早就给出了答案:所有的来访者都有一个部分不想来接受帮助,一个部分想要接受帮助。心理咨询师是与想要接受帮助的那部分自我结盟,共同帮助来访者战胜不愿意接受帮助,不愿意改变那部分自我。因此,当一个来访者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时,你可以看成是来访者想要改变,想要得到帮助,想要活下去那个部分的自我正在向你求助,你的回答至关重要。如果你愿意帮助他,你可以回答“YES”;如果你回答“NO”,你是把伸出求救之手的那部分来访者的自我重新推回不想接受帮助、不愿意改变、不想活下去那部分自我的怀中绞杀!这当然是心理学范畴的思考与解读,是对整体的人的范畴的思维,而不是把来访者当成一种疾病的思维模式。所以,做为职业咨询师,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YES,我愿意帮助你。”这并不代表我的全能,而是代表我愿意与来访者想活下去的那部分自我结盟,共同帮助不想活下去的那部分自我去成长和改变;或者,帮助来访者想活下去的那部分自我在与我的关系当中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自我,一个健康并且愿意活下去的自我。当然,这是一条崎岖、艰难和漫长的道路。如果一个心理咨询师敢说他包治百病,敢接下所有的案例,宣称可以拯救一切不想活了的来访者。专业领域内的人会如何看待他?可能会觉得他需要去接受个人成长——他全能自恋得不轻,需要心理治疗的委婉说法。或者,觉得他更像一位宗教界人士而不是心理咨询师。说他更像宗教界人士的意思是他就像“懂王”一样,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上帝。 专业内的争论我们暂且摆在一边,那是心理咨询师在从业前就需要做好的基本功课,也是从业后需要一生持续修炼(形式也包括了个人成长与督导)的基本课程。这与我们今天的论题并没有真实的关系。 对于已经从业的咨询师来说,这个论题其实真正意味着的是:我们面对来访者的求助行为时最基本的职业态度。 面对来访者求助时的肯定态度,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只包括了咨询师的个人态度。因为心理咨询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咨询师与一个来访者之间的互动。但其实,在这个职业的助人活动过程当中,每个合格的执业心理咨询师背后,都站着一群人,他并不是孤军奋战。 哪一群人?执业的专业咨询师,通过学习和培训与全世界最优秀的心理咨询理论结盟,当然也就是与创建这些理论的优秀大师们结盟;通过督导,与更多专业的咨询师结盟;当咨询师发现自己专业能力实在不能胜任与此来访者的工作,还可以通过转介,让更适合这个来访者的咨询师接手继续帮助这个来访者。曾奇峰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们咨询师都是在打群架!因此,对这个问题第一问的回答,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个咨询师个人的信心,代表的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有一百多年行业积累的专业自信!如果没有这个自信,我们的职业也是一场笑谈。 因此,如果咨询师面对来访者的求助时,没有这种自信的肯定,我反倒觉得这个咨询师应该接受个人成长或督导。他可能的确存在着自我不肯定的问题,就好似许多学习了十几年都不敢开始帮助来访者的心理咨询学习者一样——永远都没有准备好! 梅一凡的遗书我读了,让我很震撼!梅一凡是谁?读者诸君百度一下自然知晓,不愿百度的,我在文章末尾也附有他的遗书。此不赘述。 做为职业心理咨询师,天天都在与“梅一凡”们打交道的心理工作者。他的个案我并不吃惊。吃惊的是,他在寻求帮助过程中的遭遇。以下引自他的遗书。 “我认为精神疾病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它不像感冒、肿瘤等疾病,疾病可以治好,但记忆没法消除,精神疾病并不是无缘无故得的,它都是由于曾经的经历而产生的。所以这本身就很矛盾。之前是在国内看医生,最开始确诊的是重度抑郁症,后来换了更好一点的医生,被诊断是双向情感障碍,然后我被要求住院了。后来每次回国都要复查开一堆药带到日本来,妈妈总是关心地问我吃了药有没有好一点、药起不起作用,我每次都很难回答,因为我觉得没用。上次回国因为疫情原因没法复诊所以回到日本之后我去了一家日本的精神科医院想要开一些药。在做完检查和谈话后,医生很明确的跟我说,他认为药物对我来说没有用,因为我的病情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病理现象,让我产生痛苦的东西已经在长达20几年的时间里融入了我的身体,不是吃药这么容易就能解决的事。说实话听完他说的话我心里挺放松的。以前没有人跟我说吃药对于我来说没用,我就坚持在吃,药很贵,但我自己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在为了吃而吃。后来我问医生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他说有聊天型的咨询,价格有点小贵,我又问那对我来说有用吗,医生说“说实话,我觉得意义不大”。我就想到之前有个人在网上说,他经过长期的治疗之后他的医生最后和他说“可能有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活着”。  (此图为后配图,图片来自网络,使用时未发现该图片的版权登记。若有侵权,请联系我们立即删除。) 引述的遗书这段话,特别是加黑划线几句话。我们可以看成是梅一凡的求助过程。在没有人告诉他精神科药物对他的,准确地说是没有“精神症状”的心灵痛苦和自杀意念,没有作用时,他一直坚持服药。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为看成是他想要帮助自己去除“没有精神症状的心灵痛苦和自杀意念”的努力,支配这种努力的,是他内在想要活下去的自我部分。在去日本的精神科复查时,与日本精神科医生的一段对话,我感觉那代表了他最后的求助行为。 是什么?让他想改变自己“没有精神症状的痛苦与自杀意念”的动机彻底被打消,而坚定地完成自杀?遗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无需我多嘴。 如果我们把他最后的求助行为语言化,可以理解成,他在询问日本的精神科医生,“我还有救吗?”。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肯定有不同的观念。 如果我们把心理障碍单纯地看成是一种疾病,就一定会得出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同样在的答案:“医生很明确的跟我说,他认为药物对我来说没有用,因为我的病情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病理现象……”。从医学的角度说,是疾病,就有一定症状,有符合疾病诊断标准的病理现象——临床表现。如果没有症状,就不属于疾病,治疗也就无从谈起(虽然,严格地从精神障碍的现象学诊断标准上看,持续的心灵痛苦、生命无意义感,持续而严重、危险的自杀意念,已经符合了重性抑郁的诊断标准)。 可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病。 回到“我还有救吗”这个问题上来。 面对“我还有救吗”这个问题,其实李子勋教授早就给出了答案:所有的来访者都有一个部分不想来接受帮助,一个部分想要接受帮助。心理咨询师是与想要接受帮助的那部分自我结盟,共同帮助来访者战胜不愿意接受帮助,不愿意改变的那部分自我。 因此,当一个来访者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时,你可以看成是来访者想要改变,想要得到帮助,想要活下去那个部分的自我正在向你求助,你的回答至关重要。如果你愿意帮助他,你可以回答“YES”,那代表着你肯定他想活下去那部分自我的意愿,并且愿意与这部分结盟而帮助他战胜不想活下去那部分自我的自我攻击、自我毁灭的意愿;如果你回答“NO”,你是把伸出求救之手的那部分来访者自我重新推回不想接受帮助、不愿意改变、不想活下去那部分自我的怀中。 这当然是心理学范畴的思考与解读,是对整体的人的范畴的思维,不是把来访者当成一种疾病的思维模式。所以,做为职业咨询师,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YES,我愿意帮助你。”这并不代表我的全能,而是代表我愿意与来访者想活下去那部分自我结盟,共同帮助不想活下去那部分成长与改变;或者,帮助来访者想活下去那部分自我在与我的关系当中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自我,一个健康并且愿意活下去的自我。当然,这是一条崎岖、艰难和漫长的道路。 理解这个部分,我们首先要对“自我”的产生稍微做一点描述。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几乎都同意“自我”产生于人际关系之中。好的人际关系产生好的自我,不好的人际关系产生不好的自我。 要证明自我产生于人际关系当中,这里举一个大家容易理解的例子。“狼孩”,具备人的全部生物学遗传特征,但狼孩在成长中没有与人建立关系只与狼建立关系,所以被发现时,连话也不会说,更不要说有“自我”了,他只有狼的行为特征。而凡是被人抚养大的小孩都有“自我”。 人不照镜子不知道自己的样子。而婴儿的镜子就是父母或抚养者,婴儿通过父母或抚养者的眼睛(镜子),看到自我。所以,快乐健康的心灵是由快乐健康的父母或抚养者构建;痛苦的自我,是由不好的原生家庭构建。 自我构建于关系当中,但“自我”一旦产生,它就成为了来访者体验、感知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工具。快乐的自我会体验到生命的快乐,痛苦的自我会觉得生命不值得。 梅一凡遗书中提到:“我认为精神疾病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它不像感冒、肿瘤等疾病,疾病可以治好,但记忆没法消除,精神疾病并不是无缘无故得的,它都是由于曾经的经历而产生的……” 他这段话我们可以解读出两层含义。第一,他肯定了他的自我是一个不好的自我,不好的自我是他不想活下去的根源;第二,这个不好的自我是他的经历构建起来了。当然,过去的经历不仅仅是与物的连结,人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导致人产生不好的感受,更多是与人的关系构建起来的自我结构与自我。 因此,心理咨询或治疗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来访者改变他的“自我”。“改变自我”,这不正是心理学或者心理咨询的范畴吗? 如何改变自我?不好的“自我”由不好的关系构建,而好的“自我”由好的关系构建。来访者在他的童年经历、原生家庭当中,没有得到好的关系,所以构建了一个不好的自我;而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正是让来访者与咨询师这个人重新建立一段关系,这段关系当然是好的关系。 所以,对于生病了的“自我”,我们可以通过“好的关系”来加以改变。 这个“好的关系”如何构建起来?来访者以前生病的自我,与父母的关系如何构建起来的?当然,是天然的亲子关系,以创建家庭和养育为目标构建起来的;而与咨询师的关系,则是以帮助来访者达到咨询目标为目的而构建起来。 因此,如果我们无法对来访者的求助持一种肯定态度时,咨询目标不肯定,咨询关系如何构建起来? 所以,面对来访者求助问题的关键一答,不仅仅体现的是职业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帮助来访者进入到咨询当中,构建“好的关系”改变来访者不好的自我的关键一步。 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建立的“好的关系”如何帮助来访者改变“不好的自我”? 精神疾患的种类繁多,但大体主要不好的关系总有类似的特征:被忽略、被虐待、被控制、被侵犯、被伤害……,被侵入、共生、无边界……,没有爱、没有陪伴、没有抱持、没有涵容、没有适当的回应等等。总之,是一个不利来访者的身心成长,被伤害的关系。咨询师与来访者所构建咨询关系,不管咨询师是哪个学派,咨询师总是在“关注”来访者,总是尽可能地在适当回应着来访者,在抱持着、涵容着来访者、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伤害、总是无条件地接纳、总是尊重……。总之,是有利于来访者的成长,是爱与滋养的关系。 因此,咨询师与来访者不管在咨询当中具体做了什么,咨询师是哪个学派,来访者从咨询师的使用的咨询技术当中受益多少,但与咨询师构建的关系本身,就具备了一种治疗意义。让来访者做为人,感受到了人的权利、感受到了被爱与被关怀,这当然是一种让来访者的自我感觉好的感受。所以,不管来访者自我不想改变那部分如何拒斥心理咨询,只要来访者一直持续地进行咨询,来访者开始很微弱的想活下去的部分都会得到滋养,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不值得,是因为生命充满了痛苦而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如果感受到了积极的体验,生命就会慢慢从不值得的体验改变为生命值得的体验。 梅一凡说得好:“让我产生痛苦的东西已经在长达20几年的时间里融入了我的身体,不是吃药这么容易就能解决的事……”。  (此图为后配图,图片来自网络,使用时未发现该图片的版权登记。若有侵权,请联系我们立即删除。) 心理学咨询的改变理论,对于改变自我。大体有两个策略,一个如我前面所述,通过与咨询师建立的好的关系,重新创建一个自我。旧的自我不可改变,但新的自我感受与旧的自我不一样。新的自我是健康并且愿意活下去的。 这样的理论描述比较空洞。举一个我的临床实例: 我的一位长程咨询来访者,一直有一个痛苦的身体症状。每天早上一醒来,就会有一种极度紧张的感觉,感觉全身僵硬,说不出的难受。 在我们的咨询进入第七年时,他终于在一次咨询会谈当中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重大发现:折磨了他几十年的症状,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我内心可能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不想活了! 但当时,我和我的来访者都没有吃惊。因为我们双方都很清楚,他在与我的长程咨询当中已经构建了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是健康并且愿意活下去的。 咨:嗯。你的自我想表达的是他不想活了。 来:是的。 发现这一点让我好吃惊。但我一点也不害怕和担心。因为发现这一点的正是我的新的自我,正是我新的自我有力量了,才可能发现这一点。 咨:是的。如果没有新的自我,旧的自我是没有力量看破这一点的,看破了无法面对。所以只能以身体症状的形式表达。 来:是的。 咨:换一个角度,我们其实可以去认可旧的自我的意愿。 来:认可? 咨:是的。自我在关系当中产生,对自我的不满可以理解成对构建自我的关系的不满。那个被你的父亲忽略的自我,肯定很不满,他不想要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不想活了。 来:哦。这下我理解我的自恋的来源了。不想要这样被父亲忽略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构建的自我,那个让我感觉自己像空气一样不存在的自我,让我感觉自己像宇宙中漂浮的天体一样的孤独无依的自我,所以否定了这个自我——不想活了。所以,我想要的是被重视,被视为宝贝的自我。因此,我就自己创建了一个我与这个世界虚假的关系,构建了一个自恋的自我。那个自我才是我满意的。 咨:…… 这位来访者与梅一凡不同,他虽然也有一个不想活下去的自我。但他找到了防御的方式--自恋,并且与世界隔离,在幻想当中生活。不想活了的自我部分,以躯体症状的方式保留下来。并且,他把这两个部分完全分裂开来,互不相识。这样,自恋的自我替代了不想活下去的自我生活,而没有让他的自我直接暴露在想杀死自己的自我毁灭冲动当中。心理疾病保护了他,或者说心理疾病本来就是保护他的一种机制--心理防御! 所以心理治疗的一种改变原理,让寻求帮助的来访者自我部分,与心理咨询师结盟,在与心理咨询师的关系当中,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健康的自我。 持这种治疗策略的咨询师,一定是人际关系取向学派的。 另外一种原理,咨询师与想帮助自己活下去的部分结盟,帮助来访者看到、理解并改变旧的不想活去的自我部分的痛苦——修复过去的创伤,改变导致痛苦持续发生的心理活动机制,并让与咨询师结盟的这部分自我逐渐变得更加强大,有力量去整合内在不想活下去的自我部分。 这是比较传统的心理咨询或治疗改变模式。 这种比较传统的心理咨询模式,也举一个临床实例: 我的另一位来访者C君。 初来时也是跟梅一凡一样,有着强烈的自杀意念。不过,与梅一凡不同的是,她有更多的症状或痛苦。她比梅一凡有幸的是,她没有遇到梅一凡的日本精神科医生,那个宣告她的自我“无可救药”的医生。 虽然前面有过几段结局不太愉快的心理咨询经历,但没有一个心理咨询师宣告她的自我无可救药。所以,她依然相信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她,虽然这部分很微弱。 我与她的结盟,与很多的来访者一样,她也会问我,“我还有救吗?我已经看了很多个医生,我都不太相信自己会变好了。也许,杀死自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的回答是坚定的:“嗯。也许,你现在不太愿意相信你还可以改变。但我,很佩服你帮助自己顽强的意志。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与我合作,不管前面道路多么艰难,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到达咨询的终点。既然,退路在那里摆着,我们何不尝试一下呢?不过,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相信你可以改变!” 心理咨询一段时间后,她获得了新的信念——非死亡的信念。但这个新的信念与想要死亡的自我部分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我们一起去探索死亡对于她的意义,发现“死亡”其实是一位母亲,一位可以在任何她痛苦的时刻给予她抱持、支撑、无条件地接纳,给予她安全感的母亲。而这种安全感,在她真实的母亲那里并没有得到。所以,死亡找到了答案,是母亲功能在她的心理上的缺失。或者说,她缺乏一位内化的好母亲,一个可以安抚和滋养自己的好母亲。很显然,她现在的母亲不具备这样的功能。而内在那个要求自己去死的自我部分,最初就是她自己创建出来的“母亲的替代品”。只是这位母亲存在的代价太高——以攻击她和索要她的生命为代价,并且越来越无法控制。 当来访者的自杀情绪与冲动行为被象征化,被语言化,被命名,并因此成为我们可以去探索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在心理上对其进行心理操作——而不是一种自己莫名的情绪和冲动,来访者的自杀意念开始下降,并且我们的咨询也找到了新的方向。 咨:回顾上次。 新的信念让你无法去死。 能死有何好处? 不能死有何坏处? 我们这次可以从这里开始探索。 来:嗯。 就是,感觉这个新的它就没有退路了。我现在好像死就是唯一的退路。 就是,以前的那个样子就是还觉得,死亡还能给我一种安全感。 就是想到…… 咨:大不了就死了。 来:对。活起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接受。在意的东西都可以不用在意。也不用对自己要求这么多。因为不用考虑这么多事情。现在活起都是得过且过。 只是现在有人希望我还活起,那我就按照他们的想法先活。一旦他们的意愿没有这么强烈后,我也可以去死。 因此,现在不是为自己而活。 不为自己而活,许多事情都无所谓了。 如果换一个信念,感觉自己要很认真去生活。再也没有借口退缩。 以前说要去死,不会觉得做了一件多么过分的事情。如果现在有新信念了,还要去死,感觉很不好。 感觉死亡像一个背后的支撑,可以大胆去做事。不用担心别人不喜欢你,你做了什么错事没有关系,反正我背后死都会接住我,你不会担心。 我也害怕死亡。 只是我想要通过死亡寻求安全感的动机让我拒绝它。 我丢下了它,没有人给我信心也没有人给我力量。 咨:我理解了。 把死亡换成母亲,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你给了一个最好的注解。 死亡,是你的退路、支撑、接纳,给予你勇气。 如果换成母亲,那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不会觉得荒唐。 …… 一年半之后,来访者新的人格模式开始建立,来访者心理状态持续进步: 咨:想说什么都可以。 来:嗯。 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变了很多的。 咨:我也感觉到了。 来:就是我以前觉得,我是什么都想做好。反倒什么也做不好。 现在,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现在,我好像学会了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就是完全不去想以前的事情。 就是,完全不去想好像要是我曾经没有做过这件事。或者,这件事我能做得更好。虽然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但我好像更多专注于现在,没有太去想过去、未来。 …… 来:是的。 我直接拒绝了。 我也没有太管,就是我觉得内心比以前强大一些了。 没有这么在意周围的人。没有想讨好每个人。 更倾向于有价值的社交。 …… 现在看起来这些比较好的变化。 我有点变得更注重自己的感受。 内心更坚定。 然后,好像变得专注于自己的事情。然后,看起来,似乎对学习好像。学习的方式与方法上,我觉得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 …… 不管是哪种模式,心理咨询师帮助来访者的起点,都在借力于来访者内心想保护自己的部分、想改变自己的部分,想拯救自己的部分,想减轻或消除自己心灵痛苦的部分——与寻求帮助的部分结盟。 因此,当咨询师面对来访者“我还有救吗”这个问题的基本职业态度,只能是一个:“YES”而非“NO”! 因此,我们现在明白了。当来访者询问帮助者“我还有救吗?”这个问题,不管对来访者自己的生命还能否存续下去,还是把握住来访者的最后求助机会,以及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良好开始,助人者能否把握,是多么宝贵、多么关键!!! 不懂的我们可以不怪,专业的事专业的人做。但对于职业的助人者来说,犯这样的错误难道不令人震撼吗?! 还有没有梅一凡?还有没有“我还有救吗?”的这类问题。 我来回答这关键一问:当然,YES!并且,做为职业助人者,职业心理咨询师,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将与你的想帮助自己活下去的部分结盟,一起面对你不想活下去的部分。而且,如果你想活下去的部分愿意坚持,我们一定可以走到咨询目标的终点!而不管,这时间是多么地漫长、这道路是多么地崎岖、复杂和曲折!! 我希望所有的“梅一凡”们能理解,只要是合格的职业心理咨询师,都做好了准备面对你与你的这个问题。我们,职业咨询师们,对我们的职业耗尽毕生心血,经年累月的学习与成长,正是为你们的这个问题和你们不想活下去那个自我而做的准备!并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还有一点话想说。 其实,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说,最无力的并不是面对提出“我还有救吗”这个问题的来访者,或者那种对自我、对心理咨询(及咨询师)都没有信心的来访者。因为不管他想得到帮助的动机会是多么地微弱,但起码我们有了一个帮助他的机会。 我们最无力的其实是:没有咨询动机的心理疾患者。因为并不是心理咨询师治疗好了来访者,准确地说,咨询师只是帮助来访者自己战胜了自己,帮助来访者自己成长了自己。我们的帮助建立在来访者愿意求助,愿意打开自己的内心让咨询师工作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来访者不仅愿意打开自己的内心让咨询师工作,并且还愿意配合和支持咨询师对其内心进行工作的基础之上。 因为我们工作的对象是人的心灵,而心灵属于来访者自己。如果来访者不愿意求助,如果来访者不愿意打开自己接受帮助,咨询师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进入来访者的内心进行工作。这是心理咨询师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伦理守则。 许多来访者被卡在对心理咨询的误解与不信任上,也许帮助他们进入心理咨询只需要更多的心理宣传工作,或者咨询师允许来访者有一个体验并选择的过程;许多来访者卡在动机不够强烈,那只是咨询时机不到,咨询师需要耐心等待来访者的咨询时机成熟;有些来访者卡在缺乏经济支撑上,也许可以寻求公益咨询的道路。 但有一些心理疾患者,自我的防御机制很强大,自我的封闭系统很强大。虽然痛苦,但内在平衡。这些来访者不缺时间、不缺痛苦、不缺少经济支撑,他们只缺乏打开自己寻求帮助的动力,这一部分来访者,才是咨询师感觉最无力的准工作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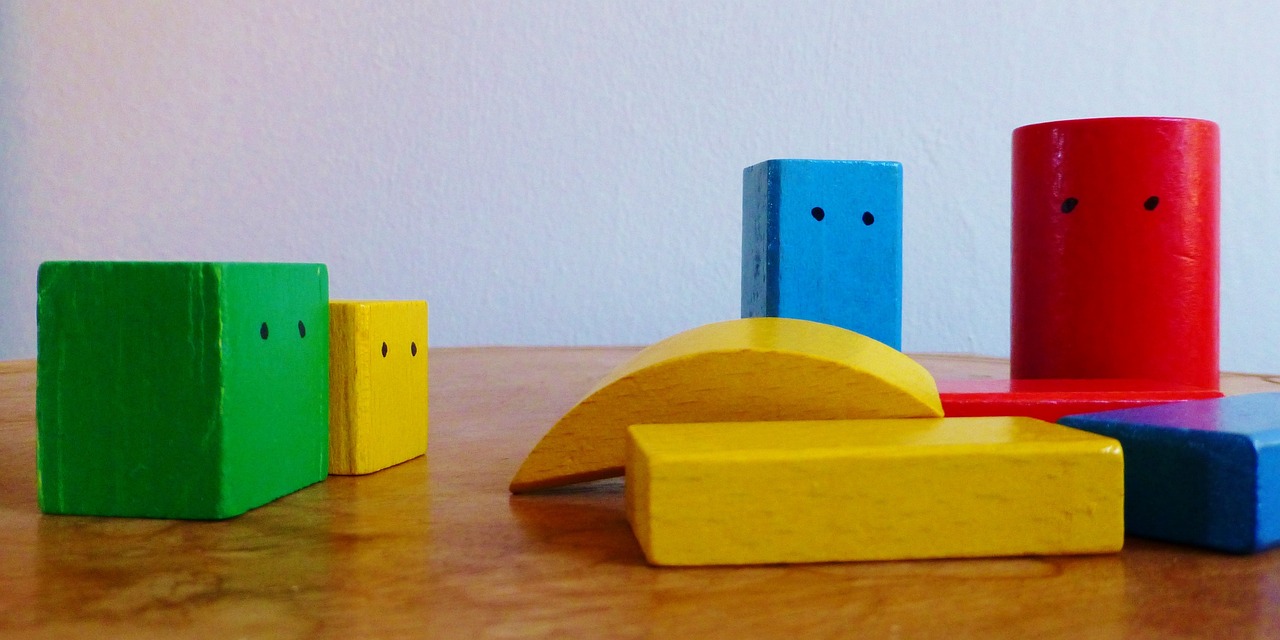 (此图为后配图,图片来自网络,使用时未发现该图片的版权登记。若有侵权,请联系我们立即删除。) 附件: 梅一凡遗书(来源于网络)梅一凡自杀遗书终于结束了。 首先想说的是,我并不是因为疫情、毕业、在日本压力太大等原因而选择了自杀。 之前也说过,在我的认知中,我的人生是一场游戏,或是一场以我为主角在撰写的小说。这并不是指这个世界在围着我转的意思,你的人生里你就这个主人公,他的人生里他就是主人公。我认为人生是虚无的,假设的,不存在的。就好比我在打一个游戏,我在这个游戏里等级蛮高的,有各种稀有装备,还在游戏里认识很多好朋友,养了虚拟宠物。但是慢慢地,我觉得玩游戏好像也挺没意思的,或者是游戏外的我因为经常打游戏脖子酸痛,再或者游戏外的我要开学了、找到新工作了没时间继续玩了。总之就是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我腻了,我觉得疲惫了,我对这个游戏不感兴趣了。我跟我游戏里的好友们说“我可能之后不打游戏了”,大家得知我要注销账号,都纷纷过来劝我“别呀!你游戏里等级那么高,以后不玩的话之前不都白瞎了吗?”“你那么多装备,都是之前辛苦抽到的,退了多可惜啊”“想想我们啊,咱们一起打游戏多高兴啊”等等,我说好吧,那我再玩一段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对这个游戏丧失了兴趣,打游戏也不会让我感到快乐,游戏外的我脖子越来越酸,越来越不想玩。我虽然还在继续玩着,但只是敷衍了事,因为我很清楚我总有一天会卸载它。这么说的话,应该能把我想说的感觉表达清楚吧。我对活着这件事,提不起兴趣。或者说,我没有任何欲望。这个欲望不是指瞬间的,短时间的小欲望,我也会想吃火锅,想化个什么妆,想和朋友出去玩。但是我没有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对生命的渴望,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未来的人生我想要怎么去归划,想要买几套房什么的,这些统统没有。因为我不想活着,所以我没有欲望,因为我没有欲望,所以我更加不想活着,这是一个循环。虽然早些年的我可能还是会多少有抑郁的表现,我觉得很悲伤或者很痛苦,但其实近几年,我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悲伤,更多的是无力感和疲惫感,我在熬着,在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过完一天算一天,这种疲惫感不是因为学习压力有多大,工作多辛苦之类的外界因素,而是来自我的内心。打个比方,你和朋友约了下午3点见面,你收拾好穿好衣服打扮好准备出门的时候朋友打来电话说突然有点小急事,约会改到6点,这3点到6点的期间你就不知道做什么了,本来以为3点就要出门所以下午也没有任何安排,头发妆都弄好了也不能睡觉,你突然觉得无事可做了,开始坐在沙发上无聊地玩手机,想着赶快到6点,可是时间过得很慢,你刷了半天微博一看时间才4点。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而我,持续这个状态,已经很多年了。这种明明不想做一件事却因为种种原因还在熬着,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地熬着的感觉,真的吞噬了我的全部,我变得一天比一天疲惫,每天都是为了过完这一天而活,每天都在靠着一点点的力气拖着我的身体确保它还在运行。我也不是不快乐,我其实挺快乐的,和朋友出去玩,看电影,刷到搞笑的视频,我都能笑得岔过气去,但这些都不是真正让我感受到快乐的东西,它就像膝跳反应一样,碰我一下我会笑,但是笑完就结束了,甚至大部分时候我在过于快乐之后反而会觉得更加的疲惫。我是一具空壳。 身边也总会有好心的朋友询问我、安慰我、开导我,“你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出去旅个游吧”“日本那个地方就是让人觉得压抑,回来就好了”,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我每次听到这种话反而会觉得更加气愤和无言。我认为自己应该属于比较能吃苦的那种类型,任何的工作在我眼里都算不上困难,哪怕搬砖,哪怕扫大街,只要挣的钱和我付出的辛苦成正比我都可以尽力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之所以很反感别人说这样的话,因为我的身体是我在掌控,我因为什么而感到疲惫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明白,我在工作学习上的疲惫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快乐,都是膝跳反应,“今天下班好晚啊累坏了”,但是睡一觉就好了,它们都不是真正让我感到疲惫的东西。我硬撑着自己的躯壳身体努力假装过好每一天,而别人总是轻松地把这些都归到工作压力太大等在我看来不值一提的外界因素上,让我觉得有被冒犯到从而更加地无力。同理,说“日本太压抑了我才会这样”的也是一样。我在几年前的无数个夜晚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让她同意我从马来西亚退学转去日本,我从到马来西亚的第三个月开始和妈妈说这件事,之后又过了一年多快两年家里才终于同意了。能来到日本我真的太开心了,我终于来了自己想要留学的国家,我可以自己打工赚点钱,也可以自己坐地铁和公交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我喜欢不需要麻烦任何人就可以自己完成所有事的大环境。这是我一直追求却在中国和马来西亚都没法感受到的快乐,因为中国有家人在拴着,而马来西亚太大太广交通也没法做到足够方便。但是恰恰我喜欢的东西好像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日本人的冷漠、日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远、日本没有人情味、日本让人觉得压抑。大家觉得是日本导致我变得所谓的“抑郁”,甚至我的父母觉得是出国让我感到寂寞受了委屈而变得“抑郁”。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没有来到日本,我可能会离开得更早,是在日本的生活让我感受到了一丝丝的生活希望,而且我在日本第一次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考上了我喜欢的大学,它让我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可能别的人对于考上好大学这件事会觉得很一般,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学习都不怎么好,任何事情都被父母插手的我来说,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考上自己喜欢的好大学是—件多么令我燃起生活希望的事。所以,不要再说日本让我压抑了,它没有使我压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救了我。我的根源性问题出在我的家庭,想要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家庭,所以我蛮庆幸早早出国的,不论是哪个国家。如果我一直都在国内甚至在本地上了大学,那我不敢想象平行世界的我有多么崩溃,甚至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我的人生啊,一直都属于一个非常扭曲的状态,就是别人看着顺风顺水,仿佛我生活中得到的所有都轻而易举,但实际上我经历的每一件好事都是用另一件事去交换的。我觉得老天爷好像看我很不爽,这是我真实感受到并且验证过也和朋友说过的,它在玩我。它对我的不好并不是那种给你一个负债累累父母离异的家庭,或者说给你一张奇丑无比残疾的身体等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不好。而是它扔给了我100块,让我去拿,趴着去捡,但是钱用线拴着,我捡一下它就往后拉一下,让我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被它耍。但是事后别人只能看到“老天爷对你可真好,凭什么就给你100块不给我,你命真好”。至少在我看来,老天爷仿佛很享受捉弄我这件事。 我在2020年初的时候确定了想要离开这件事,我想在生日417那天离开。我辞掉了当时的工作,开始做一些收尾动作。我想要死在一个平和的时期,我不想死在一个混沌的时间段里,因为我很讨厌听到别人说“她是因为xxx(外界因素)压力太大自杀了”这种话,又或者说我想给我自己的小说撰写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尾。然后呢,在我做完决定之后,开始疫情了。当时疫情还仅限于中国没有扩展到全世界,我说那我回日本吧,日本还算平和,等我回到日本之后,日本疫情开始爆发了。因为想要死在一个安稳的时期,而且觉得疫情期间死的话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困扰,爸爸妈妈可能也没办法来日本给我处理后事,考虑到这些原因我决定将我的计划往后推迟一些,等疫情结束了再离开吧。紧接着,疫情一直在持续,而且身边有人自杀了,日本明星也自杀了,新闻上每天都是在报道xx地方学生跳楼等,自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甚至前两天还因为有人自杀而上了热搜,这个时期变得越来越不平和了。老天爷很清楚我不想死在一个这样的时期,所以它在我做了决定之后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扰乱我的计划。在此我想说一下,我不是说别的死去的人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是扰乱我计划的外界因素,在他们的人生里他们就是主人公,而在我这边我是这个主人公,这个世界是由以大家每个人为不同的主人公而重叠起来的。我也不是没想过老天这样做可能是想要挽留我,但是仔细想了一下还是比较确定它就是想耍我罢了。看我连死都不能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时间点,看我连死都如此地被动,看我每天内心痛苦的纠结,或者看我因为想要死在一个稳定的时期所以暂时取消了今年的计划然后继续浑浑噩噩的活着。我之前不是没有崩溃过,我在夜里气得快要抓狂,我明明早早地就做了这个决定,为什么从那之后就开始一直发生事情,为什么要让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做的事变成了看起来像跟风别人的无脑举动、自杀效应,变成了混乱2020年死的众多人里的其中一个,我为什么连死都不能死在一个自己想要的时间,我这一辈子为什么都在被耍,我到底错了什么事。后来我不想管了,我说了要走就是要走,我不再在意别人是否说我因为疫情压力太大而死,也不想管是否死在一个很多人自杀的年份,这是我对老天最后的反抗,如果连死都要被它左右,那我的人生真的很失败,既然活着时的选择我没有办法顺我自己的意,那最后这次总可以吧。 11.5的时候我自杀了,我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就差最后一步的时候被发现了。哈哈,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对这个世界从失望变成了失望透顶。从那开始到现在的三个月里,我一点都不觉得侥幸或者幸运,每发生一件让我烦躁的事我都会把它归到如果当时死了就不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死亡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大事,它只是我选项里的其中一个。生命对于我来说其实挺不重要的,电脑卡住了那就重启,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那就结束好了。所以我并不是因为悲痛欲绝、被爱情所伤、对人生绝望等原因选择了冲动自杀,我对这个事情看得挺淡的,或者说是无所谓,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我甚至毫无异常,每天嘻嘻哈哈,该上课上课、该工作工作,吃香喝辣逛街拍照。可能在部分人的眼里,并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这篇文字是我早就写好的,然而我在11.5号那天自杀未遂之后,一点都没有劫后余生的感觉,只有更加地崩溃,我从那天之后的所有不受控制的情绪,都是因为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我之前不是没有想过“要不就好好活下去”,但在每一次鼓起勇气好好地生活之后都会产生更大的疲惫和厌恶,我放弃挣扎了。我认为精神疾病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它不像感冒、肿瘤等疾病,疾病可以治好,但记忆没法消除,精神疾病并不是无缘无故得的,它都是由于曾经的经历而产生的。所以这本身就很矛盾。之前是在国内看医生,最开始确诊的是重度抑郁症,后来换了更好一点的医生,被诊断是双向情感障碍,然后我被要求住院了。后来每次回国都要复查开一堆药带到日本来,妈妈总是关心地问我吃了药有没有好一点、药起不起作用,我每次都很难回答,因为我觉得没用。上次回国因为疫情原因没法复诊所以回到日本之后我去了一家日本的精神科医院想要开一些药。在做完检查和谈话后,医生很明确的跟我说,他认为药物对我来说没有用,因为我的病情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病理现象,让我产生痛苦的东西已经在长达20几年的时间里融入了我的身体,不是吃药这么容易就能解决的事。说实话听完他说的话我心里挺放松的。以前没有人跟我说吃药对于我来说没用,我就坚持在吃,药很贵,但我自己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在为了吃而吃。后来我问医生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他说有聊天型的咨询,价格有点小贵,我又问那对我来说有用吗,医生说“说实话,我觉得意义不大”。我就想到之前有个人在网上说,他经过长期的治疗之后他的医生最后和他说“可能有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活着”。 最后我想说,死亡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对我来说不是,我终于获得了解脱,也真的很快乐。总有人说自杀的人很想不开,其实我觉得吧,不是想不开,而是想得太开了。我的游戏结束了,但游戏本身还再继续,只是有一位玩家注销了账号而已,人类本身就是单独的个体,活好自己的人生玩好自己的游戏才是最重要的,还在游戏里的朋友们要继续好好玩游戏哦! 我先走啦,拜拜。 梅一凡 2021年2月16日 ........................................................ ................End........................................................................... -*-*-*-*-*-*-*-*-*-*-*-*-*-*-*-*-*-*-*-*-*-*-*-*-*-*-*-*-*-*-*-*-*-*- 如果孤单迷茫黄手帕愿伴你成长 原创文章 转载须注明出处 图片素材源自网络,如有侵权,立即删除 -*-*-*-*-*-*-*-*-*-*-*-*-*-*-*-*-*-*-*-*-*-*-*-*-*-*-*-*-*-*-*-*-*-*- 如果需要帮助,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找到我: ·电话:023-89009815 ·邮箱:865273090@qq.com ·QQ:865273090 ·网址:www.hspxl.cn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华大道99号长安锦绣城26-20-9(江北新牌坊转盘附近,加洲花园、电子校旁) ·微信公众号:黄手帕心旅 --*-*-*-*-*-*-*-*-*-*-*-*-*-*-*-*-*-*-*-*-*-*-*-*-*-*-*-*-*-*-*-*-*-* 重庆心理咨询-重庆心理医生-重庆抑郁咨询-重庆焦虑咨询-重庆强迫咨询-重庆情感咨询-重庆夫妻咨询-重庆青少年咨询-重庆家庭咨询-重庆性心理咨询-重庆人格障碍咨询-重庆人际关系咨询-心理咨询师-重庆黄手帕&心旅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了解更多可以关注黄手帕老师个人公众订阅号:黄手帕心理 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关注,更多好文等您分享!!!  咨询师黄手帕简介: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毕业,西南大学应用心理学在职研究生;2002年获得重庆市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重庆市心理学会会员,重庆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高级签约咨询师;重庆黄手帕&心旅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办者;职业心理咨询师。 心理动力学取向心理咨询师,参加过精神分析、认知行为、存在人本、催眠、意向对话、沙盘、箱庭、正念、叙事、短程焦点、萨提亚两性关系、NLP、EAP,团体辅导、团体心理治疗、同性恋等各种专业培训。 接受个人体验一百余小时,接受各学派、各种类型的专业督导300余小时。 在十余年万余小时的个案咨询中,以心理动力学为主导,整合所学各个流派的理论与技术,结合人生经验和工作经验,形成了自己相对成熟的咨询风格。 工作理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陪伴和帮助来访者去经历解除心理痛苦的过程,获得成长,享受人生。 咨询专业领域:自杀危机干预,抑郁、焦虑、强迫、恐惧、疑病等各种情绪障碍,神经症、人格偏移(边缘、自恋、依赖、回避、分裂样等)长程心理咨询;失眠/心理创伤/居丧/人际关系问题/各种适应障碍/亲子关系/情感婚姻/发展性危机/同性伴侣问题/同性恋自我发展问题/性心理问题咨询等。 工作感悟: 心理咨询需要把我们的内心贡献出来为来访者工作,因此修炼自己的人格和学习一样,是从事这个职业所需要的永远止境的成长,感谢来访者愿意与我们一起成长。 |
通知公告:
- 离婚了,怎么给孩子说? -2024-06-21
- 我要你为我骄傲--咨询结束十年后与来访者的对话 -2024-09-18
- 拖延:化解自恋冲突的如来大法--拖延症背后隐藏 -2024-09-10
- 饕餮、蛋壳与大象--长程心理咨询的本质 -2024-08-19
- 自恋导致的自卑、抑郁和社交恐惧——隐匿性自 -2024-08-14
- 你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你应该去S!--从小做到大 -2024-08-06
- 死亡母亲——症状的保护机制与积极意义 -2024-06-26
- 伴全能之无能感——无法言说的“全能痛楚” -2024-06-24










